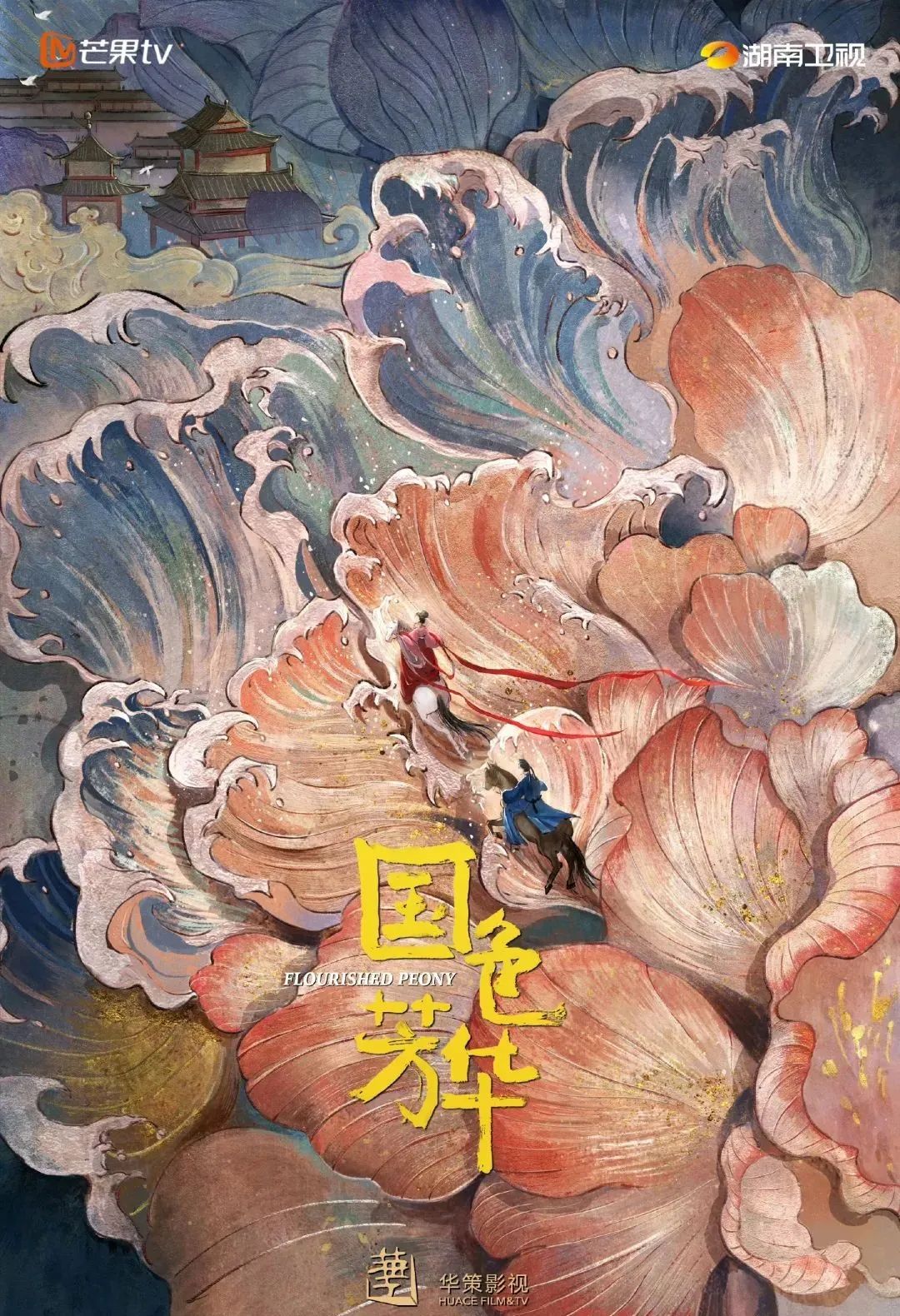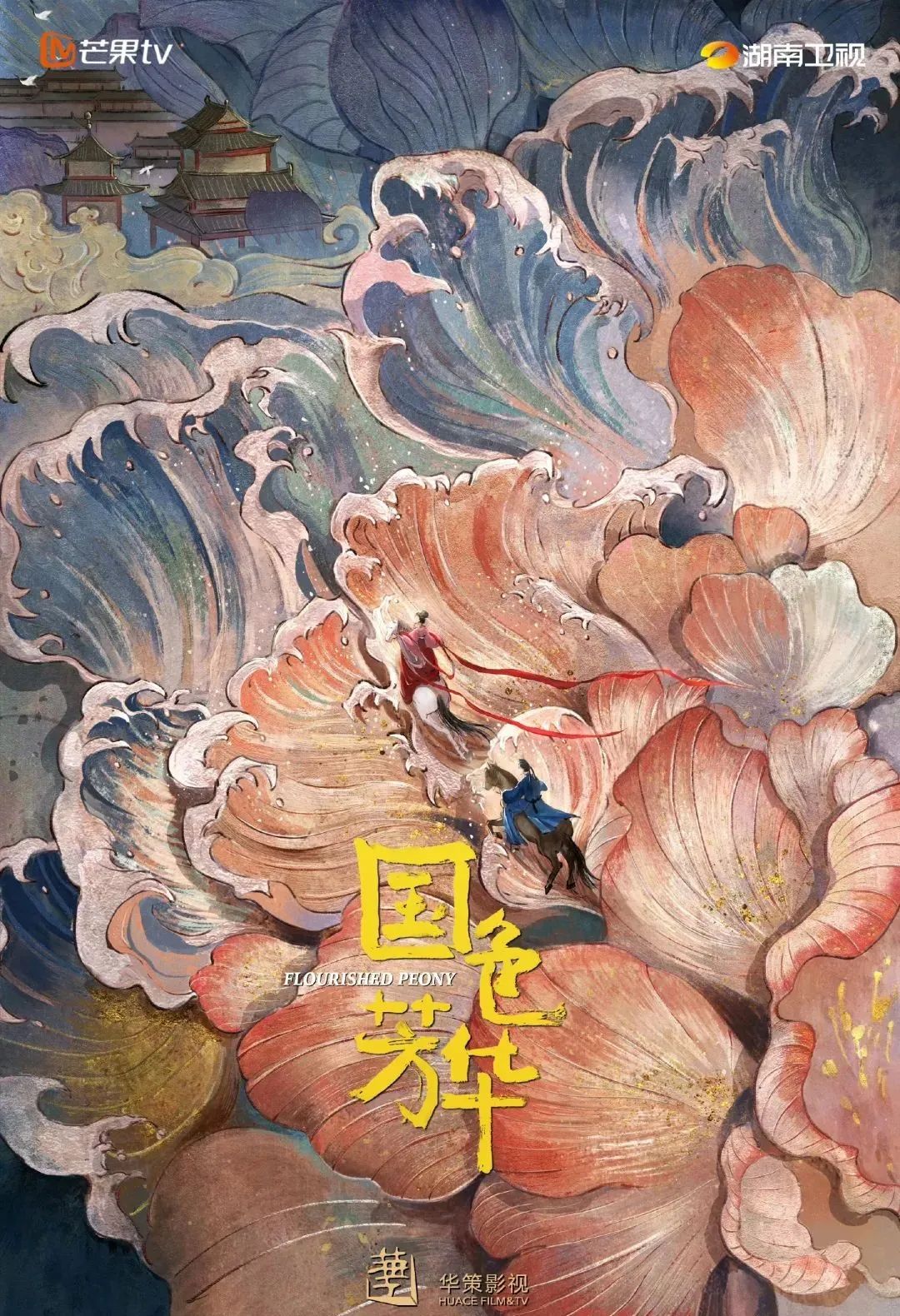藝評|從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到熒屏傳奇:《國色芳華》的改編實驗與文化突圍
湖南文聯(lián) 2025-02-17 09:12:04
從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到熒屏傳奇:《國色芳華》的改編實驗與文化突圍
文|何世華

近年來,隨著IP影視化的熱潮席卷全球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改編劇已成為國產(chǎn)劇市場的中流砥柱����。從《瑯琊榜》的權(quán)謀江湖到《慶余年》的時空交錯�����,從《知否知否》的宅斗風(fēng)云到《長月燼明》的仙俠虐戀�����,這些作品的成功不僅證明了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商業(yè)價值�����,更折射出大眾文化對類型化敘事的旺盛需求�����。在此背景下,湖南衛(wèi)視推出的開年古裝大劇《國色芳華》引發(fā)廣泛關(guān)注——這部改編自起點大神作家意千重的同名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劇集�����,以“唐代女性+牡丹商戰(zhàn)”的獨特設(shè)定,在古裝劇同質(zhì)化的紅海中開辟出了一條新航道�����,憑借精彩劇情�����、精良制作和演員的出色演繹�����,成功吸引了大量觀眾����,成為又一部由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改編的佳作。 改編的起點:從“技術(shù)流爽文”到“女性史詩”的敘事重構(gòu) 《國色芳華》的原著誕生于2011年“女頻技術(shù)流”網(wǎng)文興起的浪潮中�����,其核心設(shè)定——以唐代牡丹栽培為技能支點的女性成長故事——既呼應(yīng)了“女主靠硬核技能逆襲”的創(chuàng)作趨勢����,又因?qū)κ⑻莆幕纳疃韧诰蛎摲f而出。原著作者意千重通過大量歷史考據(jù)與牡丹栽培的專業(yè)知識,將何惟芳的成長線錨定于唐代的市井煙火與士商博弈中�����,既保留了網(wǎng)文的“爽感”�����,又賦予文本一定的歷史厚度�����。 
然而�����,從文字到影像的轉(zhuǎn)化�����,必然面臨敘事邏輯的重構(gòu)�����。劇版《國色芳華》選擇了“去宅斗化”策略:原著中何惟芳與劉家妾室的復(fù)雜爭斗被大幅刪減�����,轉(zhuǎn)而強化其與蔣長揚的商戰(zhàn)聯(lián)盟及女性創(chuàng)業(yè)群像的塑造�����。這一改編雖被部分書粉批評為“背離原著精神”�����,卻更符合當(dāng)下觀眾對“大女主劇”的期待——弱化內(nèi)在傾軋����,聚焦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。例如�����,劇版將何惟芳的婚姻困境從“借劉家氣運治病”改為“八字聯(lián)姻”�����,并通過“三年之約”的設(shè)定�����,直接凸顯其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決心,這種“現(xiàn)代女性意識”的注入����,既是對原著的升華,也是IP影視化的必然選擇�����。 但改編的爭議亦在于此:原著中何惟芳的成長依托于唐代社會對女性經(jīng)商的有限包容����,而劇版則通過“花滿筑”姐妹創(chuàng)業(yè)團(tuán)、蔣長揚“超能外掛”等設(shè)計����,構(gòu)建了一個近乎理想化的女性烏托邦。這種“懸浮感”雖增強了戲劇張力����,卻也削弱了歷史邏輯的合理性。 文化符號的視覺轉(zhuǎn)譯:牡丹美學(xué)與盛唐想象的矛盾 牡丹作為貫穿全劇的核心意象����,既是敘事的動力,也是美學(xué)的載體�����。原著以牡丹栽培技術(shù)為“硬核”支點,從嫁接技藝到品種命名�����,如“姚黃”“魏紫”�����,均以專業(yè)細(xì)節(jié)支撐女主的“技術(shù)流”人設(shè)�����。劇版則進(jìn)一步將牡丹升華為視覺奇觀:從對稱構(gòu)圖的宮廷花宴到市井花坊的斑斕色彩����,牡丹的“富貴”意象被轉(zhuǎn)化為盛唐美學(xué)的視覺符號����。制作團(tuán)隊甚至為保障花卉拍攝的真實性,制定了跨地域的花材供應(yīng)方案����,這種“沉浸式美學(xué)”追求�����,讓劇集在古裝劇同質(zhì)化競爭中脫穎而出�����。 
然而����,美學(xué)的高光之下����,歷史真實性的讓渡成為隱憂。劇中蔣長揚與皇帝“哥們式”的君臣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、何惟芳與現(xiàn)代無異的獨立宣言,均使故事與唐代的時空背景產(chǎn)生疏離�����。這樣的處理�����,使得劇集里的盛唐仿佛只是徒有其表的華麗空殼,雖然堆砌了大量符合盛唐審美的元素����,卻未能深入挖掘那個時代獨特的政治生態(tài)、社會風(fēng)俗與思想觀念�����,更像是借了“盛唐”之名����,來講述一個套著古裝外衣的現(xiàn)代故事����,難以讓觀眾從中真切觸摸到歷史真實的脈絡(luò)。這種“以美代真”的策略����,雖能俘獲觀眾感官,卻也引發(fā)“歷史虛無主義”的質(zhì)疑�����。 《國色芳華》的改編試圖在“女性創(chuàng)業(yè)”與“古裝偶像”之間尋找平衡����,但二者的沖突始終存在����。一方面�����,劇集通過“花滿筑”姐妹互助����、何惟芳“濟世救民”的抱負(fù),試圖打造“女性群像+家國情懷”的宏大敘事����;另一方面,蔣長揚“無所不能”的男主設(shè)定����、男女主“英雄救美”的情感模式,又讓故事滑向傳統(tǒng)古偶的窠臼�����。 
這種矛盾在人物關(guān)系上尤為顯著:原著中蔣長揚是“皇帝的暗士”,冷峻深沉����;劇版則將其改為“花鳥使”,性格圓滑機靈����,與李現(xiàn)的現(xiàn)代氣質(zhì)結(jié)合,雖增強了角色魅力�����,卻弱化了權(quán)謀線的邏輯�����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����,何惟芳的每一次危機幾乎都依賴蔣長揚的介入化解����,這種“偽大女主”敘事,暴露出改編者對女性獨立性的理解局限——女性的強大仍需男性強權(quán)的背書����。 《國色芳華》的改編爭議����,是網(wǎng)文影視化進(jìn)程中經(jīng)典問題的縮影����。在“還原”與“創(chuàng)新”的尺度把握上,書粉批評劇版將何惟芳與家人的親密關(guān)系淡化����,把其原生家庭改為冷漠疏離,這一改動雖強化了“逆境覺醒”的戲劇性����,卻犧牲了原著中“家庭支持”對女性成長的意義。在“爽感”與“深度”的平衡方面����,原著借牡丹栽培細(xì)節(jié)、商戰(zhàn)謀略營造“技術(shù)流爽感”����,劇版為追求節(jié)奏緊湊,簡化專業(yè)邏輯����,致使“妙手回春救牡丹”等情節(jié)被批“魔幻”�����。
盡管如此�����,《國色芳華》的探索仍具啟示性:其通過牡丹美學(xué)構(gòu)建的文化辨識度�����、對女性互助敘事的側(cè)重�����,為古裝劇提供了新思路�����。正如意千重所言,影視改編“讓故事在新時代的土壤中開出新的花”�����。若未來IP改編能更注重歷史邏輯與女性敘事的自洽,或可真正實現(xiàn)“國色”與“時代精神”的共榮�����。《國色芳華》的改編實驗����,恰似牡丹的培育過程——既需尊重種子(原著)的基因,又需適應(yīng)新土壤(影視市場)的養(yǎng)分�����。它未必是完美的“國色”�����,但其以美為盾�����、以女性成長為核心的敘事嘗試����,仍為IP影視化提供了有價值的樣本?���;蛟S�����,真正的“芳華”不在于復(fù)刻歷史的每一片花瓣�����,而在于讓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神�����,在當(dāng)代觀眾的心里扎根綻放�����。責(zé)編:周聽聽
一審:周聽聽
二審:張馬良
三審:周韜
來源:湖南文聯(lián)